

作者 | 魏一白
周末北京人形机器人马拉松活动结束之后,很多朋友都在讨论,其中一个话题就是,为什么一定是人形机器人?
从最早波士顿动力的Atlas系列,到特斯拉的Optimus,再到现在Figure AI、宇树等等国内外厂商,机器人的形态设计中,“人形”设计似乎被视为通用机器人的终极形态,这个结论,也有机器人公司创始人在讲。
人形机器人真的是最优解吗?在过去一年的机器人热潮中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。
现在来看,人形机器人的形态设计可能只是技术与意识形态局限下的过渡方案,而机器人的未来,应该是一种跳出“人形”框架的“拟态”机器人——一种自由度极高、形态可根据需求无限变化、完全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具身智能系统。
一、人形机器人设计:通用性的权宜之计
人形机器人之所以成为主流,源于其在当前技术与市场环境下的“低门槛通用性”,目前表现在几方面。
一个,讨论最多的是,要适配人类环境。目前人类生活环境,基本上都是为了人类身体结构所设计、适配。之前行业交流时,一家医院负责人曾说过,要部署机器人,医院很多东西需要重新改造,单是“门把手”的改造成本就需要数百万。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工具,也都是如此,是为了适应“人”而设计。
当前,机器人如果要直接与人类生活环境交互,“人形机器人”是最合适的形态。
第二,人机交互自然性和用户接受度。人形形态对于人类来讲,有天然亲和力。人形机器人通过模仿表情、肢体语言,能在服务、医疗、陪伴等场景中提升用户接受度。日本软银的Pepper机器人便是典型案例,其人形设计增强了零售和护理场景中的情感连接。

第三,技术依赖度。当前机器人的技术发展,无论是模仿人类动作姿态的强化学习,还是给予基于人体解剖学的机械设计,人形设计大多是依托或者说依赖生物学、物理学和AI的现有成果在发展。
第四,是市场与文化的影响。这一点和第二点类似,人类对机器人接受度,或者预期,与市场和文化相互影响。大量科幻作品(如《终结者》《钢铁侠》),塑造了公众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。对于机器人厂商来讲,迎合这一文化现象,能够很好地提升产品吸引力,提升融资前景。
这些因素使人形机器人成为当前通用机器人研发的首选。
人形机器人形态的设计看似通用,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。
即便是适配人类环境,依然会存在很多功能方面的约束。比如,人形机器人受限于人类身体的物理限制,双足行走不如四足稳定。当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,效率都不如轮足,这也是行业里大家常质疑的,为什么工厂落地应用不用轮足而用双足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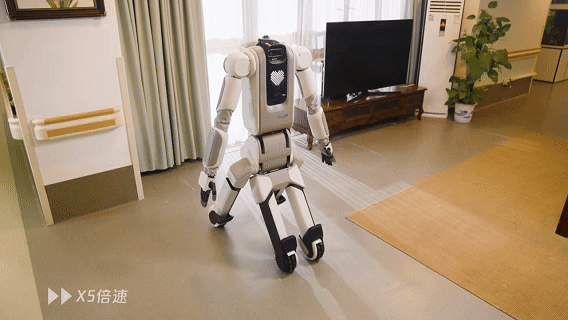
(腾讯机器人“小五”采用了多足设计)
另外,灵巧手当前的发展水平,距离高自由度机械爪(如工业机械臂)还差很远,灵活度、效率都比较差。
效率,是当前被诟病最多的表现。人形机器人虽能覆盖多任务,部分场景任务的成功率也确实在不断提升,但是单项任务的效率未必高,甚至远落后于人类或其他形态的机器人产品。
一个关键质疑是:如果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,人形形态真是最优解吗?
二、“拟态”机器人:跳出人形框架的终极通用性
“拟态”机器人的理念
“拟态机器人”,我们把它定义为一种自由度极高、形态可根据任务需求无限变化、完全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具身智能系统。其核心特征是摆脱固定形态的束缚,能根据环境和任务动态生成最优形态结构。
《变形金刚》中有个角色叫幻天灵(Amalgamous Prime),能变成任何形状,从人形到车辆、武器,甚至抽象结构,展现了“拟态”的终极通用性。
用“拟态”一词,希望大家跳出“人形”框架的思维范式,彻底以功能和结果为导向,不受任何预设形态限制。例如,它可能在平地用轮式移动、在狭窄空间变成软体、在交互场景模拟人形,甚至分解为微型模块执行分布式任务。
国外有一家机器人公司,叫Nio Robotics,他们旗下机器人Aru的形态既不是人形也不是四足,是一种可变幻可组合的机械臂+轮式形态。Aru的机械臂,在机器人行进时可以是腿,在机器人工作时可以是手臂。末端执行器也是可以搭配不同的夹爪或者灵巧手。
这款机器人有了“拟态机器人”的雏形。
除此之外,还能够看到有“拟态机器人”影子的产品包括:
哈佛大学的软体机器人Octobot,可以通过气动驱动实现柔性运动,能适应狭窄空间,展现了非刚性形态的潜力。斯坦福的藤蔓机器人可通过柔性结构延伸,适合探测任务。
MIT的模块化机器人M-Blocks通过磁力连接实现自组装,能动态重组为不同形态。
“拟态”机器人的理论优势
“拟态”机器人通过动态适配性和功能整合,解决了人形机器人设计的局限:
因为形态的多样性,能够做到全场景适配,覆盖不同场景下落地应用的工作需求,例如,在地震废墟中,它可变成蛇形穿梭缝隙、重组为人形、四足搬运重物,甚至可以变成千斤顶、防护罩抢救、保护幸存者。
在工作时,可以根据任务目标实时调整形态。例如,在矿物探测场景中,可以从轮式(快速移动)切换为钻头状(采集样本),无需预设固定形态。
冗余性与鲁棒性优势,即使部分模块损坏,它仍能通过重组维持功能,类似生物的自愈能力。
最重要的一点,“拟态”机器人是效率优先。“拟态”机器人的目标是以最优路径解决问题。例如,上楼梯时,它可能沿扶手“流动”或吸附墙壁爬行,而非一定是人形或四足机器人的步行动作上楼。
三、“拟态”机器人的应用场景
在落地应用上,可以说“拟态”机器人,因其动态适配性将会覆盖我们可以看到、想象到的任何场景。
除了目前大家常看到的工业、商业场景,可以再分享一些特殊场景。 极端环境,比如在深海、太空、核辐射区,它可变形为流体状钻入裂缝,或重组为高强度结构抵御压力。
救援与灾难响应场景,在地震废墟中,它可变成蛇形穿梭、重组为人形搬运,或形成防护罩。
医疗场景,作为微型机器人群进入人体,动态调整为手术刀、探针或药物载体。
工业与物流场景,在工厂变为人形使用工具、在仓库变成轮式搬运、在管道变成软体检修。
探索与科研,在未知环境中(如外星球),它能生成全新形态,解决传统机器人无法预设的问题。
尽管“拟态”机器人理论上能覆盖所有场景,以下场景可能仍然是人形机器人的方向,或者说这些场景的专用形态就是人形机器人。
比如情感交互,在家庭陪伴、心理咨询等场景需人形特征(表情、肢体语言)以增强亲和力。“拟态”机器人虽可模拟人形,但抽象形态可能降低情感连接。
四、“拟态”机器人面临的挑战
技术瓶颈
一个是控制复杂性。
人形机器人已面临双足平衡和灵巧手控制的难题。“拟态”机器人需要实时优化更多自由度,涉及复杂的运动规划和动态重组。“拟态”机器人需要超强AI实时生成形态和控制策略,当前AI(如强化学习)在多变量实时控制上仍有限,需要持续突破。例如,强化学习结合生成模型可让机器人“想象”并实现新形态。未来AI大模型的发展可能解决多自由度动态优化问题。
第二个,“拟态”可能需要自由组装甚至可编程材料的发展。
“拟态”机器人需要可编程材料(如液体金属、记忆合金、电活性聚合物),但这些技术多处于实验室阶段,成本高且不稳定。例如,3D打印材料虽能自组装,但刚性和耐用性不足。
“拟态”机器人也可能由微型模块组成,通过磁力、化学键或AI协调实现动态重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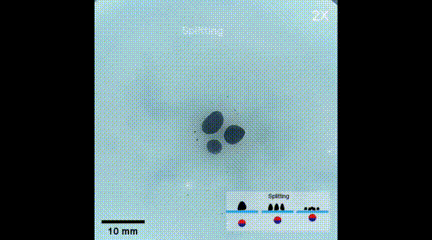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个,当前已经存在的问题,能源效率。 当前人形机器人、四足机器人的续航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,而“拟态”机器人的多样性变化和多自由度驱动耗能巨大,需新型能源的出现。我甚至认为,即便固态电池发展起来了,也未必能够满足需求。 最后,是产业链的发展,主要是在制造上。 人形的机械结构和供应链虽然还没标准化,但产业链已经逐渐成熟,而“拟态”设计需要全新工艺,需要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。 人类中心主义深刻影响了机器人设计,主要表现为“以人为模板”的路径依赖。 一个是意识形态带来的设计惯性。人类倾向于模仿自身形态和行为,导致机器人设计陷入“人形至上”的范式。例如,门把手是为人类手掌设计的,机器人也默认模仿人手操作,而非探索更高效的方式。未来的机器人厂商,需要摒弃“模仿人类”的思维,聚焦任务目标。 另外就是,借鉴自然界(如章鱼、水母、蚁群)或非生物系统(液体、电磁场),设计超越人形的形态。例如,模仿变形虫的机器人可能比人形更适合狭窄空间。 第二个是人类环境局限带来的功能设计限制。很多人讲,设计成人形,是为了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已经为人类打造好的环境。但以人形为模板,肯定会限制机器人各类场景中的潜力。还是说上楼梯,为什么一定要用脚走上去?不能攀爬扶手翻上去吗? 文化和市场对人形机器人的偏好,使得机器人的创业者、研发人员,忽视了非人形或“拟态”设计的可能性,延缓了真正通用机器人的到来。 从商业化前景角度看,人形机器人已经有了一些(想象出来的)清晰的应用场景(家庭助理、工厂工人、护理),容易吸引投资。特斯拉、Figure等公司的人形机器人项目获得巨额融资,证明了投资人的认可度。 而“拟态”机器人短期内,认可度低,投资风险高。而机器人厂商,显然会更倾向于“看得见”的成果(如Optimus、Atlas)。 这一点,未来两到三年,我认为大家会慢慢对人形机器人这个形态祛魅,会逐渐认可混合形态机器人的应用。比如轮式+人形,会是机器人落地应用形态的一个阶段。慢慢大家会聚焦于真正解决问题的机器人需要什么样的形态,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人形。 同时,在一些特殊作业场景,会开始出现一些“异形”机器人。 举个例子,今年年初有扫地机器人厂商,推出了带有机械臂版本的扫地机器人,把扫地机器人从智能清洁领域推向了家庭服务机器人方向。这也会是一种发展路径,机器人的形态一定是可变化的。 整体来说,短期,2-5年时间,人形机器人还是主流,“拟态”机器人可能仅在高价值场景出现、试验。中期,5-10年,模块化或混合形态机器人作为过渡,逐步改变市场认知。长期,10-20年以上,“拟态”机器人开始出现,不过要成为主流,取代大部分机器人形态,可能要30年以上。 一个必须要承认的事实是,机器人是工具,即便是人形机器人,本质上是工具。因此,机器人的形态设计,必须要以目标为导向,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,效率优先。 人形机器人作为当前技术与文化的产物,其形态设计是权宜之计,但其局限性——功能约束、效率问题、意识形态束缚——表明它只是过渡方案。 真正的通用机器人应是“拟态”机器人:一种自由度极高、形态可无限变化、完全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智能系统。意识形态束缚
市场与投资逻辑
结语:机器人是工具,形态设计需要以目标为导向


关注公众号
即时获知最新推送
休闲时刻
陶冶艺术情操
Copyright © 20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Network.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:数智化网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翠微中里14号楼
